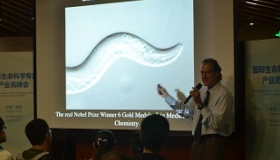中传媒VS港中大(深圳) 南北两高校同题讨论青春文学
获国际安徒生奖之后 南北两高校同题讨论青春文学的得与失
文学与青春包裹下的曹文轩
“恰同学少年”80后与90后是我青春对话
时间:4月25日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活动中心
林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师):本次研讨会的缘起,在于近期曹文轩老师的获奖将儿童文学和青春文学又一次带入了大众的视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少年儿童文学体制的发展脉络,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了一大新变,即“青春文学”这一文化现象的崛起。以《萌芽》杂志及其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主导,在种种青春文学期刊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合力扶持下,青春书写蔚然成风,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与狂欢。这群1980年代出生的少年作家被称为中国新一代的文学代表。随后中国作家协会将“80后”作家纳入体制,青春文学自此正式登堂入室,进入严肃文学的研究视野。我自己亲历了80后写作的盛行,与好友都曾创作、出版过青春文学作品,也因此得以进入北大中文系,所以对这个议题有特别的情结。而你们是95后一代,某种程度上见证了青春文学的没落。希望借助本次讨论,呈现两代人对于青春文学不同的经验记忆,从而探讨和反思青春文学的意义、价值与出路。

能说青春文学是好的文学或者不好的文学吗?
卢韵(经管学院大一):《萌芽》陪伴了我的少年时光,然而现在再读《萌芽》,发现笼罩全书的都是“淡淡的忧伤”,故事情节存在相似的套路。随着时间推移,青春文学是否有些异化?“新概念”本是为打破应试作文的窠臼而设,然而自身也逐渐不可避免地流于模式化。感觉80后还能表达出少年对世界独立的思考与质询,而90后大多数选择了去模仿。
陈洁儿(经管学院大一):我认为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与时代有很大关系。80后与90后成长的环境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相差的十年足以改变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与生活的习惯。80后的青少年时期互联网还未普及,读书、写作、投稿是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而90后成长的时代已步入一个崭新的世纪,互联网时代的迅速到来以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冲淡了写作的作用,少年们开始寻求其他方式表达自我。
段然(经管学院大一):我觉得如今的“泛娱乐化时代”对新概念作文大赛影响力的减弱,或者说参赛作文质量的下滑有一定责任。快餐式的文化体验与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让人们的精神感触愈发迟钝。商业化所带来的功利心理也让青春文学的创作不再纯粹,甚至陷入了创作模式的窠臼中。
陈敏(经管学院大一):微博、微信、QQ空间这些网络平台给青年们提供了太多可表达想法的途径,以至于思考与表述越来越碎片化,来不及沉淀,其中理性、逻辑,甚至情感的力度当然就会相应减弱。
陈佳雯(经管学院大一):我想到了美国“垮掉的一代”,他们的作品很多时候也是在讲述青春时期的骚动,但对比国内的青春文学,两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不是因为题材上的不同,而是本身的文学价值就有高低之分。
李修齐(经管学院大一):对我来说,真正的青春文学应该像福克纳说的那样:“通过鼓舞人类,唤起人类原有的荣耀、勇气、荣誉、希望、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去帮助他们学会忍耐。”反观国内大多数青春文学,或许包装精致,又或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但缺少的恰恰是对“人类原有的荣耀”的描写,以至于读后就忘,内心空虚。
张晨辰(经管学院大一):我们能说青春文学是好的文学或者不好的文学吗?如今有些青春文学写手戏称自己以前的作品为黑历史。到底是因为作者从少年走向青年,心智愈发成熟?还是仅仅因为青春文学不是“好的文学”?我反而认为,正是当年少年人懵懂的眼光,“浅薄”的思考,反映了生活,亦反映了时代。这不是对苦难的书写,不那么深刻,然而青春文学让少年们在最懵懂的时候感受到了生活的艺术性,这正是它的功劳。无论什么文学都无法跳出自己所在的时代背景,通过阅读这些文字,重回那些岁月,或者感受另一种青春,也是青春文学的价值所在。只有郭敬明、韩寒才配拥有青春文学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写小文的年代,都有自己的青春文学。

应该学会利用商业视角去推广优秀的青春文学作品
丁若虚(经管学院大一):曾经我们认为青春文学的文学性逐渐被商业性所覆盖,但不能忽略的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商业性回归文学性的趋势,那便是利用商业的力量,推动文学的发展。通过公司的包装,包括明星经济学和书籍的设计装帧,增大文学作品的吸引力。如郭敬明的ZUI最世文化打开了青春文学市场,开始通过“文学之新”大赛挖掘新的青春文学作家,之后通过版面设计与包装,打造“明星写手”吸引消费者,使青春文学发展为一个产业,盈利超越传统的严肃文学,常年占据销量排行榜的前列。韩寒监制的ONE app也着眼于发现新锐作家,然后将文章出版成书,同样在考虑占据市场份额盈利。而文学与影视的互动,通过电影的改编,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点对严肃文学也有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学会利用商业视角去推广优秀的青春文学作品。
周亚楠(理工学院大一):对比一下中外关于商业化的态度,西式玄幻冒险、日式ACGN产业链等,都有极强的商业化特点,人们也消费得乐此不疲。而为何中国青春文学一旦商业化便饱受诟病?在青春文学商业化十分可行的时代背景下,保留文学性不应该成为一种束缚。从国外的成功经验如《哈利·波特》、《暮光之城》等等来看,青春文学市场广大,但是中国始终没有找到商业化与文学成功的结合之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文学商业化的诉求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潮流,这就要求作者在某一程度上需要迎合市场需求。但文化更多时候是与市场脱节的,经济发展过快,文化标准却依然受到很多限制,太过保守,对于青春文学的包容性不够。
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没落深感惋惜
张思静(特邀嘉宾,曾蝉联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在谈论“新概念”时我们喜欢将它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视之为发掘和扶植新一代写作人才并改变文坛风尚的契机。然而我始终认为,“新概念”应该放在教育史而非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谈论,如果没有中国教育界过分重理轻文的环境,就不会有“新概念”的激动人心。
与此相关,很多人说“新概念”的没落是因为青春文学的没落,然而我始终觉得真正导致“新概念”没落的是它不再和高校招生挂钩。这并不是说参赛者都是怀着纯粹功利的目的来参与比赛,事实上,曾经的“新概念”对参赛者最大的吸引力来自于它所昭示的文理平等的理念。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竞赛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激发或推广了任何新的文学概念,或者为文坛带入任何青春的元素,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评判体系,在对错分明的应试世界里,加入了对个性的诉求。我想,对于我们那一代在“新概念”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生而言,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不管有没有亲身参与比赛,对它的存在都是心怀感激的:在性格成型最关键的时期,我们被告知试卷和题集不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道路;独立思考和质疑权威是值得嘉奖的品质;叛逆并不是一种罪恶,而获得师长的认可也并不需要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新概念”的没落深感惋惜。
王玥(经管学院大一):父母对我们阅读的介入,反而将我们推向了一些作品。青春中的我们渴望脱离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我们逐渐找寻到身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意义。这种心理让我们与很多青春文学中反叛的主角产生了共鸣,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青春文学受到青少年追捧很重要的一点。
张莉萍(翻译研一):其实回想读青春文学的日子,我一点也不羞愧,相反,我觉得那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充满怀念,甚至有点骄傲。青春是一种状态,青春文学刚好满足了那个年龄段的情感需求,是对青春的一种记录,这是青春文学最大的意义。现在它们被陆续拍成电影电视剧,走向市场化,正说明了它们具备一定的魅力和市场号召力,我们也往往借此消费青春,缅怀青春。
记录/张嘉霖 整理/李修齐 高逸枫 林峥 摄影/彭文颖

他的获奖对于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
时间:4月26日
地点:中国传媒大学52号楼101室
颜浩(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刚刚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这是继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文学的又一殊荣。作为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曹文轩小说的关注重点和审美特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他的作品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他的获奖对于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将围绕这些重点问题,进行全面客观、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与讨论。
曹文轩所写的成长不是一种真实的成长
顾彦秋(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我想主要从三个关键词来谈曹文轩小说的特色。第一个词是“苦难”,表现童年时期的苦难是其作品最显著的特征;第二个词是“美”,这种美是古典的、诗意的,作家写苦难也遵循美的原则;第三个词是“成长”,曹文轩笔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经历了成长,在苦难中,更是在深重的孤独感中成长。但我也认为,曹文轩所写的成长并不是一种真实的成长。如《草房子》中的杜小康和细马,一个孩子在面对“家破人亡”这么巨大的苦难时,真的能完成那种成年人都自叹不如的处变不惊、坚韧不拔的成长么?我觉得是令人怀疑的。
杨灵敏(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如果说曹文轩的小说有哪些打动我的地方,那一定是在人美景美的苏北水乡发生的悲剧故事,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庄严感与沉重感,这或许是区分其与一般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标志所在。读曹文轩的小说让我获得了一种真实的感动,这种感动来源于书中人物超越普通意义的成长挫折和苦难经历。然而,苦难叙述不应仅仅作为一种审美手段,它的背后应当有更深刻的历史形态的展现。如《草房子》中秦大奶奶的一生,不仅是个人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但曹文轩并没有完成这个人物的塑造,最终让这个满腹仇怨的老太太被油麻地的人情美给感化了。将苦难写得如此惊心动魄,战胜苦难的过程却被轻描淡写地处理,实在令人遗憾。
无疑会将他的乡村书写
带入某种虚幻的境地
张培培(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读曹文轩的小说,最容易感受到“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古典情致,这来自于作者赋予人物的苦难体验。但我认为小说中的苦难并没有被刻意渲染和夸大,而是用诗意的环境淡化物质贫困、生老病死的悲哀,用悲悯的情怀突出人性的善良和灵魂的纯净。曹文轩的小说追求的“美善合一”和西方文学追求的“美真合一”是有区别的。他的小说的古典美是人物自然人性的散发,这与作者将文学的审美教育和人性教育融合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曹文轩小说的阅读对象大多为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在发展,但是精神追求还很模糊,尚未形成完整的价值观,他们对小说中描述的苦难没有切身经历,但却能被其中善良美好的人性所感染和吸引,我认为这就是少儿文学应当完成的目标。
种晓阳(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我认为曹文轩小说里的“真和美”是一致的,并没有刻意夸大“美”而牺牲“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要放在作品所表现的环境中,我们现在对作品中“苦难”的展现所生发出来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当下、并且指涉当下的。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苦难”就是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形态,人与人之间就是体现出那样的人性之美。所以曹文轩的小说世界是真实的,它展现的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而不是我们基于当下对“真实”的定义。当然,作品肯定有文学化的表达,但我认为那是基于现实、真实合理的美化。
谢擎矞(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我认为曹文轩小说在古典美的外壳下,有意对乡村世界进行了美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他对城市的刻意“塑造”-——城市是作为乡村世界的对立面存在的。这种对乡村的美化和对城市的贬抑是基于曹文轩“美比真更重要”的创作观,但这无疑会将他的乡村书写带入某种虚幻的境地。景致优美、人情醇厚的油麻地是一个“桃花源”,在这里保存了作者对于美好世界的全部想象,但这个油麻地与现实中国是脱节的。作为读者,我可能会被油麻地的人和事所感动,但很难被震撼。
徐小(首都师范大学2015级文艺学专业博士生):一般认为曹文轩是一位颇有古典风情的作家,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有非常现代的一面。以《根鸟》这部作品为例,它的主题是追问人为什么活着?为何追求这样深刻的终极命题?答案是什么?作家自己可能并不明确。这就一点不“古典”。因为古典时代个体的价值是明晰的。只有在现代语境下,个体存在的意义才成为了问题。伊格尔顿在《人生的意义》中指出,人活着的意义在于他人。而根鸟活着的意义在于自我完善,曹文轩是以一种审美关照的方式来看待苦难的。这确实很崇高,但也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对于苦难缺少反思,根鸟两次上当被归结为“他就是一个轻信的人”,让人怀疑他的理性有没有在苦难中成长起来。二是极度张扬自我会导致他者的客体化。如果将苦难的审美意义过分拔高,就会导致对苦难的透支。
缺乏儿童文学应有的奇幻或者“秘密”的东西
顾静燕(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我认为在谈论儿童文学时,首先应该确认“儿童是什么”。儿童这个概念本来就是被创造和被赋予的。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儿童有好奇心,而在于羞耻心,正是羞耻心和仪式感将儿童和成人分隔开来。但随着电视和网络的普及,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本来被认为属于儿童的那种简单、不成熟和本来应该属于成人的复杂、成熟的东西渐渐趋同。其实这在曹文轩的小说中也能看到。尽管这次曹文轩获得的是安徒生文学奖,说明他的小说依然被视为儿童文学,但在我看来曹文轩小说中缺乏儿童文学应有的那种奇幻、或者“秘密”的东西。
张晓燕(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曹文轩曾评论过当代文学中的“作坊情结”,认为以“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寻求自己在文坛的立足之地,是拿“土特产”与人相争的路数。但是反观他的作品,其中就充满了“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田园格调的苏北水乡、柔弱纯净的古典女性。也正是这些带有鲜明地域色彩和中国特色的故事,成为其最终得到西方文学体系认可的原因。安徒生奖选择曹文轩,正如同诺贝尔文学奖选择莫言一样,折射出西方对中国的审美想象只来自于古典、传统的那部分。
除此之外,中国在现代化进程所走过的道路、当代文化呈现的纷繁特点都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它们在审美过程中被遮蔽和忽略了。这种忽略也说明在西方价值体系中,中国文化理所应当是一个停滞、永远传统且只能传统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曹文轩小说中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否体现出作者对于西方世界中国想象的刻意迎合?
曹文轩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历来是备受争议的。尽管他做出了解释,称自己是以美学立场而不是性别立场来塑造女性形象。但是我认为他的解释似乎不足以说明他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男性中心立场。那些女性不论是作为引导者(如温幼菊)、陪伴者(如纸月),还是引诱者(如秋蔓),都仅仅是男性成长过程中的陪衬,缺乏自身应有的独立意志。女性只能成为一种模式化、类型化的符号存在于男性主导的世界中,这不能不说是曹文轩小说重要的价值缺陷。
整理/颜浩 摄影/房玉刚